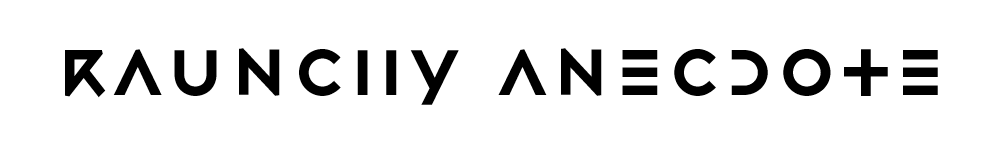我的意識明明還算清楚,身體卻呈麻痺狀。
完全沒有感覺,硬梆梆的,像是在水族館內隔著玻璃觀賞箱內的大鯨魚一樣。
把手貼在玻璃上,感覺冰冷,看著鯨魚在藍色的水裡悠遊,無法明白他的感受。
雖然知道是自己的身體,靈魂卻幽幽飄浮起來。
雖然知道是自己的身體,靈魂卻幽幽飄浮起來。
我想這可能是鬼壓床也說不定。我的兩眼直勾勾地望著天花板。
忽然房門被打開,透出一絲微光。
有些昏暗,我看不太清楚走進來的人是誰。
大概過了好幾秒,父親的臉龐出現在我的右手邊。
我看著父親,父親看著我。我無法說話,父親也不說話。就這樣又過去了幾秒。
父親接著把右手輕輕放在我的頭上。
十五年從來沒對我做過如此溫柔的動作的父親,正不發一語地揉著我的頭。
或許是因為身體麻痺的關係,我對這個觸碰感到很不真實。
從小,我對父親的印象就是不苟言笑,似乎嚴肅的話題之外沒有別的事能引起他的注意。
直切面、橫切面、線條、方形,他的思考里大概找不出任何有弧度或圓滑的地方。
對於家庭教育也是如此,非黑即白,典型軍事主義。
我們從小就明白凡事必須循規蹈矩,對長輩說話要輕聲細語,對同輩要相互忍耐,對家人相敬如賓。
我們從小就明白凡事必須循規蹈矩,對長輩說話要輕聲細語,對同輩要相互忍耐,對家人相敬如賓。
而此刻,父親親暱的動作使我臉紅心跳宛如初戀的少年。
我不知道父親是否也抱持著同樣的感情,他只是木然地撫著我的頭髮,以手代梳穿插髮間。
忽地,像是想起了什麼,抑或是為了確認些什麼,他把手抬起,賞了我一巴掌。
清脆紮實的一巴掌。
父親站在床沿看著我,臉上依舊沒有表情。
我從迷茫中詫然回神。
我很震驚。但是完全感受不到痛楚。
眼睛也無法再更驚訝。
只是面無表情地繼續躺著。
就像我父親的臉一樣,是沒有五官的臉。兩張臉。
父親像是肯定了,於是轉過身去。
再回身時,左手多了一把刀。父親是個左撇子。
在我還無法釐清一切之前,我看見父親用刀朝我的右手劃開一筆。
像水墨畫師著筆畫出山巒綿延一般,行雲如流水又鏗鏘有力。
血沿著缺口滴滴答答地積累在地上,形成一個血漥。
我的口甚至連一聲哀嚎也無。
我面無表情地睨著父親面無表情地用左手拿著刀子割著我的右手。
不論內心多麼震撼也沒有表情。
要是此刻有一個陌生人走進我的房間,看到這個畫面肯定只會覺得是什麼臨時搭建的劇場,兩個專業的演員正在演對手戲吧。
痛楚這時才像暮年的驢子一般緩緩地襲向我,某種不知名的感受在我的喉嚨深處瘋狂跳躍著。
莫名地我竟渾身發癢。
「嗚...嗚嗚......呀...啊......」
我的視線開始模糊,眼皮開始大幅度地抽搐,眼球不受控地往上翻。
我的視線開始模糊,眼皮開始大幅度地抽搐,眼球不受控地往上翻。
失去意識前,我用盡力氣望向父親,那是我多年來第一次看見父親露出滿意的微笑。